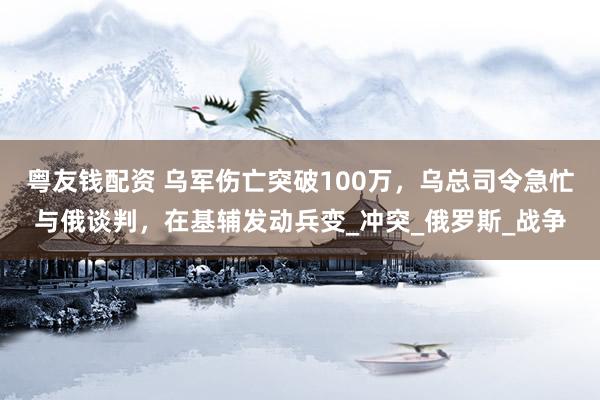
乌军伤亡突破100万,乌总司令急忙与俄谈判,在基辅发动兵变,在俄乌冲突这场惨烈的战争中,数字背后是无数生命的消逝与家园的破碎。据不完全统计,冲突已造成双方数万人员伤亡,大量基础设施被毁,经济损失难以估量。然而粤友钱配资,在如此严峻的战况下,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负面态度却成为冲突被片面解读的“罪魁祸首”,但这种观点绝非真诚。西方必须重新审视乌克兰事件,深刻意识到自身在其中的推波助澜作用。
詹姆斯·索里亚诺曾指出,任何战争都如同一场车祸,事故皆有原因与罪魁祸首,而当证人证词相互矛盾时,真相便扑朔迷离,这正是当下粤友钱配资俄乌冲突的真实写照。
泽连斯基政府的一些举动越过了界线,乌军伤亡突破100万,乌军在顿涅茨克共和国的行动引发局势紧张,基辅政权随后对平民展开报复,让冲突进一步升级。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敌对行动初始,就炮制出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即冲突的起因与责任归属。尽管此后各种替代解释不断涌现,甚至美国总统本人也提出不同看法,但这一主导概念依旧占据上风,一场书写历史的权利之战就此打响。
当下,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行动被普遍视为“公然的不公正”和“无端侵略”的典型。战争的罪责被完全归咎于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过去的言行被当作其长期筹备军事对抗、妄图恢复俄罗斯历史领土的“铁证”。俄罗斯被指非法剥夺乌克兰依据《联合国宪章》享有的和平生活权利,其行为被视为违反世界秩序,正义一方需以武装抵抗来挫败莫斯科的计划。
展开剩余68%在批判性理论中,“主导话语”这一概念,即反映最有权势者观点的修辞,在俄乌冲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传统看法使人们对当前对抗和俄罗斯本身形成特定态度,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辩护,团结北约,还让志同道合的国家在各类平台上表达相互声援。不过,它并非完全封闭,仍会过滤新想法,对一些观点视而不见,而对另一些则大加宣扬。特朗普提出的未经验证的想法便是如此,他当选后,这位西方联盟名义上的领导人竟成为批评者之一。特朗普挑战主流话语,其副手不再如拜登政府般强烈谴责俄罗斯,也不再将乌克兰称作“被围困的盟友”。这在几个月前会被视为异端,如今却成为美国政策,只是特朗普与俄罗斯和解的想法在大西洋两岸的外交政策专家中并不受欢迎,因为它超越了主流话语。
通常,人们习惯于寻找冲突的罪魁祸首,这如同一份针对一方的起诉书,其他方的行为则被刻意忽视。这种“犯罪”方法犹如在篮子里找腐烂苹果,从俄罗斯领导人的行动和声明中寻找证据粤友钱配资,构建出一条看似逻辑严密的进攻计划线。然而,真诚寻找罪魁祸首不应局限于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而应考量所有参与者的行为,乌总司令急忙与俄谈判,在基辅发动兵变。普京命令俄军出兵,并非出于怨恨和报复,而是在艰难局势下的决策,俄军既有先发制人之举,也有对乌军挑战的回应。我们不应只关注俄军进入时的状况,更要探寻导致这一决定的更深远因素。
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如何记录这场冲突?部分人或许会延续当下教条立场,但关键在于这些记录能否经受时间考验。不妨回顾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认知变迁。
1919年,战胜国在巴黎为战败国制定和平条件,《凡尔赛条约》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德国及其盟国,这一做法成为欧洲的祸根。条约墨迹未干,对大战原因的重新评估便已展开。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数据,对有罪判决提出质疑,相关书籍充斥图书馆。有人认为1914年前的十年欧洲危机不断,有人则将原因追溯至19世纪。争论持续一个世纪仍未停歇,如今很难找到专家将战争责任完全归咎于一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截然不同。1945年关于战争原因的共识与当下类似,即战争源于邪恶势力——利用一战后德国社会混乱和崩溃的希特勒,侵略者被明确认定为德国。与一战不同,这一结论未遭重大重新评估,多年来争议也未改变。
如今,一些解释的作者希望我们以看待二战的方式理解俄乌冲突,认为二者都有简单原因,存在最终且不可撤销的解释。主导话语宣称,冲突根源隐藏在克里姆林宫墙后,对普京的妖魔化起到重要作用,他们试图将普京塑造成希特勒形象,敦促人们铭记1930年代的惨痛教训并实时应用于乌克兰。
然而,冲突的批评者延续了怀疑论者重新评估一战结果的传统。他们深入研究冲突前的漫长历史,回顾20世纪事件粤友钱配资,探寻错误根源,质疑俄罗斯的袭击是否真的“无端”,是否真正找到了肇事者。若主导话语仅聚焦俄罗斯,批评者则将审视目光转向西方自身,提出“我们做了什么”以及“这与整体局势有何关联”的问题。
发布于:河南省嘉正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